高教名家名篇
易竹贤:涉足学海,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
论及中国当代的胡适研究,不能不提武汉大学的易竹贤先生。易竹贤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和胡适研究专家,尤其是他的胡适研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率先在此领域取得标志性成果的先行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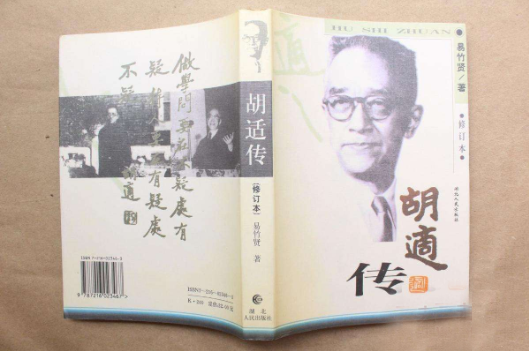
一、半个世纪的学术道路
易竹贤先生1935年生,湖南湘乡人。在中学读书时,他听语文课老师李运昭女士讲解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很受感动,由此产生了对鲁迅的敬仰之情,并喜爱上了文学。1952年,他从湘乡初级师范毕业,到一所小学教书,1955年调到邵阳专署教育科当干事。1956年,国家发起向科学进军,他以调干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之所以选择中文系,便和喜爱鲁迅有相当的机缘。1961年大学毕业,他留校当教师,先是教写作,担任写作教研室副主任,后抽调去搞“四清”,不久又作为教学革命小分队负责人被派到武汉肉联厂工人大学教书。
1975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鲁迅博物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绍兴等地相继成立了鲁迅研究小组,他是武汉鲁迅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实际由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成员由工农兵和教师构成,他是其中的教师代表之一。武汉鲁迅研究小组的办公地点在湖北省委宣传部,所做的工作是编印《读点鲁迅》,出了两期,期间还编印了《鲁迅论文艺》(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在鲁迅研究小组工作期间,他把《鲁迅全集》通读一过,这为后来的鲁迅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8年初,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先教了一阵马列文论,选编了《马列文艺理论著作选》(铅印讲义)。后去教中国现代文学,并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陆耀东、唐达晖先生一起着手修改刘绶松教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初创期的代表性教材之一。但受时代的局限,这部教材的内容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主要问题是以“左”的政治观点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抬高左翼文学,而对一些艺术上有成就、思想观念上与左翼不同的作家和作品持否定的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满足恢复高考后的教学需要,提议对这部教材进行修改,重新出版。由于刘绶松教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修改的任务便落到了陆耀东、易竹贤、唐达晖等刘绶松教授的这些弟子身上了。
易竹贤先生承担的是修订这部教材的五四文学革命及鲁迅等部分。他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鲁迅、胡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思考。这种思考是时代所激发的,也是时代所给予的机会。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思考;但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勤于探索的精神,没有以前打下的厚实基础,也不会有这样的思考。易竹贤先生和当时一大批学者一样,借着时代春风,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一片土壤里耕耘,他的付出获得了回报。
率先撰写和发表的有分量的一篇论文是《试论鲁迅早期思想和文艺观》(载《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对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文艺观进行了新的考察。他认为,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是研究鲁迅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研究鲁迅的思想是我们“知人论世”、研究和评价鲁迅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还因为鲁迅的思想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典型性。他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新文化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基于这一基本观点,他提出鲁迅早期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战士”,其政治思想“经历了由赞成维新改良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鲁迅早期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基础形成的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鲁迅的“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思想,具有启蒙主义的性质,必须放到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待。鲁迅的这一思想,明显地是受到尼采的影响,但又与尼采的思想有根本性区别,其积极的意义是把个性解放和“立人”当作挽救祖国危亡和改革社会的途径。文章的结尾,他强调鲁迅早期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一面有其局限性,一是“鲁迅在论述文化发展或社会发展的历史时,还没有(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也还不可能)做到从社会的物质产生的客观存在来说明,他往往是从文化本身的条件或外部条件来说明的”;二是“在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改革社会的力量时,心目所注的是少数英哲天才,而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他的视野中却尚未获得一个应有的位置”。很显然,这个评判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当然也可看出那个乍暖还寒时代的思想印记。
紧接着发表的是一篇引起更大反响的论文《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就来自他修改刘绶松教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其主要的意思在1978年到一所高校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讲过。文章提交给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他在大会报告后即被《新文学论丛》看中,分2期在该杂志刊出(1979年第2期、1980年第1期)。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开始正面评价胡适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他强调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不是改良主义的代表,而是“反对宗法专制旧文化的战士”和“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如提倡白话文学正宗、文学形式大解放和实写社会之情状,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胡适的白话诗文创作,有开风气之功。总之,胡适在文学革命中是立了功的,有重大贡献。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是传达了一种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评价胡适的强烈声音。
从此开始,易竹贤先生着手进行系统的鲁迅研究和胡适研究。他的这些研究,主要是结合教学来进行的,是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的一个成果。
由于给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易竹贤先生对鲁迅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时,是一边讲课,一边写讲稿。他联系鲁迅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鲁迅早期思想的性质和特点外,还有鲁迅与进化论、《天演论》的关系,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的关系,鲁迅世界观的转变,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鲁迅,鲁迅的文艺思想,鲁迅的人格等。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写出了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专论。这些成果大部分先行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①],1984年又以《鲁迅思想研究》交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界的前辈李何林先生看到这个书稿后很高兴,欣然为该书作序。他在序中说这部书稿有“新颖和独创之处”:“关于六十年来研究的历史概略,关于‘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的对比研究等,尤为少见。作者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位中年教师,比较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反对长期以来‘左’的流毒,也反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思想比较解放,实事求是,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②]中国鲁迅学会顾问林辰、复旦大学陈鸣树、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夏明钊、澳门的谭任杰等,也先后写信、或著文肯定和褒扬这部著作[③]。
要特别提出的是,《鲁迅思想研究》第五章,是一篇《“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之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写于1980年4月,发表于《鲁迅研究》1981年第3辑,后稍作修改补充,改题《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收录。张梦阳教授在这本书的长篇论文《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中这样写道:“鲁迅、胡适比较论开始得不早,论文也很少,然而却有一篇专论进入了思想文化的较深层次,这就是易竹贤的《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易竹贤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资料周详,条分缕细,分析深入,观点全面,注意从文化观念上进行比较研究。”[④]他花费1200余字对这篇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的特点做了重点介绍。
可以看出,正是循着鲁迅和胡适比较研究的思路,易竹贤先生转向了胡适研究,开始了他在学术上更为重要的探索阶段。所谓“循着”,这里主要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评价标准上的一个承先参照。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春风虽然已经吹起,但是人们对极左的思想批判运动仍记忆犹新,评价长时期来被视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胡适,难免心有余悸。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易竹贤先生从鲁迅研究中确立起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从中国现代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中获得了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认识,从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既然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要从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加以充分肯定,那么,在文学革命中事实上影响决不下于鲁迅的胡适为什么不能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加以肯定呢?《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一文,正是从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思想原则上对鲁迅和胡适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革命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又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思想发展道路。把握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是这篇文章的精彩处,比如强调鲁迅和胡适“共具爱国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却有反抗与幻想、崇拜两种态度”,他们“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共同反对封建主义,而态度有彻底与‘周旋’之分”,他们“共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诗文,而存在注意内容变革与偏重形式改良的差别”,他们“学术研究上曾互相借鉴,互相尊重,共同讨论,态度和方法却有原则的区别”,他们“同受进化论的影响,鲁迅循革命道路前进到马克思主义,胡适循改良主义而堕入反革命泥坑”。作者在文末“简要的几点结论”中特别指出:“处在帝国主义侵略蹂躏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效力的,其中不仅包括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也包括像‘五四’时期胡适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因此,在中国,应该而且可能建立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十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如此。”显然,在1981年思想解放才刚开始的年代,在人们对一些教条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作者采取了一些策略性的语言,带着一些过去时代的思想痕迹,但其主要的方面却是勇敢地冲破思想牢笼,为胡适“评功摆好”,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要系统地研究胡适,先必须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和整理。为此,易竹贤先生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找出了尘封已久的十数本胡适著作(他说由于长期被封,找出来的胡适著作落满了灰尘),又到胡适的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到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寻找胡适的资料。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数量可观的胡适著作。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胡适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2、3期)和《胡适著译书目系年》(载《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做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他才动手写《胡适传》。《胡适传》1987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再版,1998年修订三版,2005年四版,受到学界广泛的好评。由于传主是个政治上敏感的著名人物,《胡适传》初版的发行还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作者在该书1994年修订版序中对此有所交待:“犹记得1987年4月,一万部精装本《胡适传》已整整齐齐,静静地躺在了书库里,却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几经周折,终于这年10月21日获准发行了。至年底2个月零10天便销售一空。反响也颇为强烈,有北京、香港、澳门、台北、纽约等地共四十余家中外报刊发表评论或介绍文字。”出版一本胡适的传记,要遭遇这样的周折,这种感慨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了,这说明时代有了巨大的进步。
因为有《胡适传》的撰写,易竹贤先生在1989年前后发表了多篇关于胡适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胡适研究论丛》)、《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月刊》1989年第5期)、《胡适与西化思潮》(《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论胡适的散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谈胡适的小说考证》(台北《国文天地》1990年第12期)、《开拓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同路人——鲁迅与胡适》(《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1990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坚持了《胡适传》的基本观点,对胡适思想的具体评价上则更为明晰地确立起了科学民主的思想原则,越来越自觉地抛弃了此前的某种含混态度,旗帜鲜明地捍卫现代性的价值观。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易竹贤先生出版了论文集《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学海涉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新文化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现代品格》、《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历史嬗变》、《民主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等论文。他更多的精力则是花在培养博士生方面,为青年学者的书作序,奖掖提携后学。
二、鲁迅研究和胡适研究
易竹贤先生学术生涯中最为学界同行称赞的,当然是他的鲁迅研究和胡适研究。
他的鲁迅研究,除上文已经提及的,我还要特别指出,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联系当时思想建设的历史实践,敢于打破陈说,思考的是鲁迅研究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谈到鲁迅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提出,“鲁迅从‘五四’时期即开始迈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步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彼消此焦油过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于是,鲁迅的唯物史观便日益成熟、完善,渗透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鲁迅后期对于国民性的认识和解剖,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认识与态度,也充分反映出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达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以人道主义一端而言,他坚持把鲁迅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认为鲁迅思想发展的早期和中期,提倡过人性的解放,接受并宣传过人道主义思想,经过1927年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也并没有否定人性的存在,对人道主义也并非一概抹煞、抛弃。“鲁迅是承认存在共同人性的,但这种共同的人性又因阶级而有差异;他后期仍然坚持解剖国民性,而又有了明确的阶级分析,便是正确地把握了共同人性、国民性(或民族性)与阶级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具体证明。”他又进一步说:“‘人道主义式的抗争’固然是软弱的,不能依靠这种抗争作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力量;但是,对于暴露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和狰狞面目,打破人们的幻想,争取社会各界对革命的同情等方面,‘人道主义式的抗争’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往往是革命者所难以直接起到的作用。”像这样把问题提到规定的历史语境中去,有现实针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和逻辑的检验的。这种态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
易竹贤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当他把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研究时,他没有忘记鲁迅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把鲁迅的这种与众不同处以“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显著特色”提了出来。他说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显著特色”,首先是“执着现实的战斗的思想家”,其次是“富于求实精神而又关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第三是“善于把深刻的思想植根于丰富的知识,并表现于生动形式之中的思想家”,第四是“严于自我解剖的伟大思想家”[⑤]。对于鲁迅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显著特色”,当然可以做不同的归纳,但这种把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普遍性一面与其独特的个性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思维逻辑的,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鲁迅思想研究》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首开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作者把鲁迅与胡适看作是两位文化巨人,对他们进行了比较,重点是把握他们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他把他们两人所走的道路概括为“同途而殊归”,这一形象化的概括,后来曾为别的鲁迅研究专家借用。这样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把比较的方法运用于现代作家的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特定的规范,而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则早已被研究者所运用。但把比较的方法明确地运用于同一个时代两个文化巨匠身上,当时却十分少见。易竹贤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鲁迅和胡适,而且他所进行的比较又紧密联系研究对象的实际和特点,没有一点凌空蹈虚,显示了独到的眼光。正是因为这一点,《“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之比较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易竹贤先生学术成果影响更大的,当是他的胡适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研究长期来是一门显学,进入新时期后成果卓著者不在少数,而胡适研究当时还鲜有人涉足。原因不外是在长期的国共政治斗争中胡适的形象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或者说是被充分妖魔化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提起胡适,人们马上会想起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御用文人。在资产阶级右派形同历史反革命的年代,有谁会去研究胡适,为他说些公允的话呢?易竹贤先生的胡适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着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凭着一份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和探索真理的勇气,开始了“筚路蓝缕”之旅,成为新时期最早对胡适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代表者之一。
易竹贤先生在为胡适作传之初就立下宗旨,他说:“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做客观公允的评价。”[⑥]他在研究中所用的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对于胡适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多方考核,酌情取舍,务必令人确信可靠的,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全予摒弃。他准备资料就花了数年时间,从今天我们看到的他的《胡适传》多种版本可以看出,“作一信史”和“按实而论”的初衷是实现了的。
《胡适传》以非常翔实的材料,全面展现了胡适的一生,对胡适的功过做了系统深入的评价。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比如充分肯定胡适在治学中的疑古精神,认为这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肯定他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做出了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创立了“新红学”。又如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胡适对国民党当局既有幻想又有矛盾。他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方面偏向国民党,但他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因而也不满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他公开提出不仅政府的权限要受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法的制裁。《胡适传》对胡适的这一主张给予了肯定,指出这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呼声,“表现出一点法治和民主自由的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再如肯定胡适在抗战中出使美国所作的贡献,指出胡适是基于民族正义,“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候,当最困难官”。虽然作为一个“书生大使”,在一些事情的处置上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胡适认真对待自己的使命,积极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坚持到美国各地演讲,做美国民众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能这样评价胡适,的确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难怪书出版后被境外看作是大陆重新评价胡适的一个信号。
现在看来,《胡适传》在学术上取得突破,主要得益于评价标准的调整。如果固守特定时期党派政治的立场,国共两党对胡适的评价是难以取得一致的,甚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因而很长时间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对胡适的评价针锋相对。但如果超越了党派政治的立场,能从更具包容性的原则出发,比如从民主主义或者现代性的原则出发,对胡适的评价两岸就能取得不少共识。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其坚持民主理念,发起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成绩不容抹杀。他在民族危亡时刻放弃不做官的宗旨,出任驻美大使,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奔走,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也是不容抹杀的。他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甚至表示过反对,但他与国民党当局也有矛盾,曾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的专权提出抗议,其捍卫民主的立场也是相当坚决的。胡适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中,他是坚守民主自由理念而行动又较为温和敦厚的一位。他的温和敦厚,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文化性格。这使他在激进的政治革命时代,常常受到“革命”态度不够坚决彻底的指责,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种不坚决和不彻底性,恰恰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征。这些知识分子后来试图走一条温和的社会革新之路,而胡适以他的中道姿态,成了这批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易竹贤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给予的一个机会,率先把评价胡适的标准调整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现代性上,突破了历史上形成的政党政治的立场,对胡适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种突破,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反过来又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历史的进步。
《胡适传》一切以事实为准绳,在资料的考证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比如,长期来大陆学界指责胡适崇洋媚外,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作者查遍胡适的著作、言论,没有发现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因而传记中不予采用。又比如,胡适30年代发表了一篇5万字的长文《说儒》,对孔子评价很高。对于以“打孔家店”而“暴得大名”者的这篇文章,台湾的一些研究者颇感困惑,有的以此来否定胡适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想,有的指责他前后矛盾。作者经过深入研究,指出这些学者是把历史人物的孔子与作为偶像的孔子混为一谈了。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化先锋,反对的是偶像化的孔子,于思想解放有大功绩;《说儒》则是对历史人物的孔子作客观评价,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是很有见地的,既坚持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易竹贤先生的《胡适传》广受欢迎的再一个原因,是它在长篇传记的散文学术性写作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胡适传》以年代分章,围绕重要史实或具有趣味的人生故事,分为72节,各节相互勾连照应,顺序推进,突出重点,编织起了胡适完整的人生图景。为了行文的简洁,作者把大量的资料,包括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存疑备考的问题,全移在注文里,注文丰富,成了这本《胡适传》的一大特色。这些注文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是后来治胡适者可以利用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把大量的史料、重要的考证及存疑处放到注文中,使正文的文字简洁,主脉清晰,这是一种新的传记体例,可以为后世所借鉴。
《胡适传》出版后,好评如潮。大陆这边,辛之勤在《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发表《具史家胆识,含风骚神韵》,对其学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龙泉明在《书刊导报》(1988年3月3日)上发文,认为该著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而且“搜索甚勤,取材甚精,判断也甚谨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人民日报》1988年3月19日发表秦志希的文章,指出该著描绘出了胡适“这一个”的独特个性,“一种强烈的真实感油然而生”。《光明日报》1987年7月4日发表《红旗》杂志社的周溯源的文章,标题即是“磨就昭昭镜,功过是非明”。《湖南日报》1987年12月5日发表颜雄、舒其惠的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胆识兼备的信史”。萧思在《博览群书》1988年第2期发表《我读〈胡适传〉》,认为该著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作者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与其对于明确的写作目标的执着追求”。刘道清在1988年1月22日的《长江日报》上发表《胡适其人和〈胡适传〉》,强调这是“大陆第一部完整详尽地传述和评价胡适一生的专著”,“有助于当代青年认识胡适其人,并进而认识历史、社会和人生”。程志坚在《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发表文章,肯定这部《胡适传》是在“文化历史座标中重朔胡适形象”。
在海外,台湾学者吕实强撰三万余字的专论,全面评析《胡适传》,认为:“作者于撰写过程,确下相当工夫,不仅参阅资料广泛,架构安排亦颇费心力,文字流利通畅,叙述简明扼要……于中国大陆上长期清算诋毁胡适之后,能撰成这样一本具有学术理想与学术水准的专书,已相当难能可贵。”他的结论是《胡适传》“实具有开拓性的意义。”[⑦]1988年4月5日和6日的《澳门日报》发表了谭任杰的《按实而论,秉公直书》,作者声称“读了这部严谨的史传文学作品《胡适传》,可以看到今天内地的学术研究课程,已经不限于一些专题,议论自由之风气,也逐渐开展起来了”。欧维之在香港1988年3月1日的《作家月刊》上发表《两岸书声鸣不住》,指出易氏的《胡适传》“力避此前成书的某些传记的小家子气,以表现中华学人应有的恢宏气度自期;同时,作者特别注意汇集传主那些传为美谈的生活细节,穿插于字里行间,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大人物描绘得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想要将胡适作为‘国民党政府领导和影响下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来写的,粗读本书,我以为他的这个愿望是达到了的。”纽约的《时报周刊》1990年2月24日至3月2日揭载李又宁的文章《胡适先生在大陆》,声称易氏的《胡适传》“在大陆很受重视”,鉴于大陆的情况,“易著是难能可贵的”。印度驻华使馆的白春晖1988年9月27日从北京的印度使馆致信(英文)易竹贤,自称不太懂中文,但他写道:“我是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珍贵文化传统的仰慕者。我有幸曾经作为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正是1947年至1950年胡适博士任校长的时候。”他在信中说:“我没有认识您的幸运。但是,我最近偶然读了您的最优秀的《胡适传》,特地写这封信告诉您,我是多么地赞赏您的书。我很高兴您不辞辛苦地搜集和筛选出一切关于胡适博士的有用材料,写出了他的生平、工作以及他对中国的有益贡献。我应该祝贺您写出了这样一本好书,以一种活泼的文体写出的一本很好的文献性的著作。更重要的是,您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客观评价的态度,写出了胡适的一切。”[⑧]
三、做学问的态度及治学风格
易竹贤先生多次在其著述的序、跋中声称,“平生景仰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也钦慕胡适先生的学问文章,激赏五柳先生不折腰故事”。在《涉足学海,纪历二三》一文中,他又写道:“在学术道路上,我所凭借的仍是农家遗留的一点讲究实际和吃苦精神,以及湘人的一点蛮性;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五老八中’一批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哺育下,也逐渐开阔眼界,得到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训练。又颇钦仰已名所涉的魏晋竹林名士,大约也感染些‘师心’‘使气’的异端色彩,并与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思潮相融合,便产生大胆补正与超越前贤的勇气,有一点点创新的成绩。”[⑨]他的这一番自评,是客观持平的。
在《涉足学海,纪历二三》中,他称做学问第一要注重材料的翔实:“我们涉足学海,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而占有材料便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工夫。只有占有充分翔实的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他以自己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一文为例,指出这是他用具体材料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次重要实验:“在文章里,我首先用胡适自己的《<吴虞文录>序》、《易卜生主义》等近十篇文章作材料,证明他最先提出‘打孔家店’的口号,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新思想的革命作用,应该说相当有说服力。其次,用同时代许多倡导者的证词。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热烈参加讨论和实践,承认胡适在当时的倡导者地位和影响;鲁迅到1927年还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无声的中国》)。这些都是直接的证人。三是以反对者的抵制和攻击作证明。如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的小说《妖梦》和《荆生》,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矛头都指向胡适。稍后,‘学衡派’的胡先骕写《评尝试集》,‘甲寅派’的章士钊写的《评析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也都指名攻击胡适。复古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认胡适为仇雠,不也从反面证明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所处的倡导者地位和他所发挥的革命作用吗?”[⑩]
“做学问讲究根底,工夫扎实,主要是指掌握材料应充分、翔实、广博。治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在占有材料方面,据我的实际体会,最要紧的是掌握第一手材料。这重要性大家都懂得,实行来却并不容易;往往会躲懒,走捷径,用别人的第二手材料,那就只能人云亦云,或跟着别人出差错。”秉持这样的理念,他研究胡适时,先花了大量工夫去搜集材料。有第一手材料做依据,比较靠得住,他心里有底,所以也就不怕别人扣帽子,说他为胡适辩护翻案。[11]
易竹贤先生做学问所追求的第二个原则,是“努力超越求创新”,但创新是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说:“人类文化事业像一条奔流不息向前发展的长河……皆因后一代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有所超越,不断积聚这些超越创新所得的成果。……我也因秉承某种‘师心’、‘使气’的异端色彩,故每有所论,必定在尽量掌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独立思考,说一点自己的见解,努力补正超越,有所创新。”[12]他关于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研究,关于胡适的研究,包括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都是循此创新原则而取得的成果。
易竹贤先生做学问所秉持的第三个原则,是“排除干扰求真理”。他介绍自己时常说“为人诚厚耿直,只认真理,不屑逢迎”,这八个字,他自称“是我人生的态度,也是我治学的态度与品格,而这些又与‘诚厚耿直’的个性相关。”[13]这种直率的表白,本身即可以见出他“诚厚耿直”的个性。他说“排除干扰求真理”,首要之点是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第二是不赶“风潮”,第三是主观上要避免武断和自以为是,要敢于超越自我。他这样说,也尽力这样去做的。这使他的论著保持了讲真话的特色,不虚饰,不矫情,实事求是,析理居正。
上述三条,是易竹贤先生自己总结的。我在此还想补充三点:
一是他的治学以实证研究为主,但论题的选择却表明他非常关注现实,而且具有前瞻的眼光,看问题很尖锐。他关于鲁迅和胡适的研究,其实都是联系着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现实背景的,提出的问题本身即体现了时代的需要。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是当时思想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它们是关系着中国的思想界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承担着某种政治风险,虽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和魄力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一些成果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被看作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开始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
二是他的精益求精、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超越。易竹贤先生对他著作中带着时代印记的一些问题在继续思考着。他在《胡适传》出版后,把新的思想所得及新发现的重要史料随时录于书中,当再版时以此为基础做了多处重要的修改。《胡适传》已经有四个版本,这四个版本对胡适的基本评价始终如一,没有改变,说明他对胡适的把握与断识是“据事直书”,经得起检验的。但一些修饰性的用语、个别的具体提法,已经做了修改,现在所见的修改后版本显然减少了初版本的那个时代的色彩,更贴近学术,更贴近胡适的实际,更能显示胡适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这种追求学术纯真的品格、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是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
三是文风朴实,文字畅达。文如其人,易竹先生的治学不仅力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力避哗众取宠、追随时尚的流风,一切皆以事实为据,以理服人,文风朴实。他自己曾私下表示,他比较满意的还是自己文字的朴实和畅达。我理解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字中有一种朴素的美。
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在易竹贤先生七十华诞时,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卓尔易公,七秩仁风。竹籁凤鸣,贤蕴和忠。文史洞识,力作甚丰。诠评胡鲁,五四传承。桃李珞珈,学界欣荣。古稀俊迈,又开新春。”温儒敏教授是鉴于易竹贤先生在鲁迅研究和胡适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对他加以褒奖的,我引用他的这首诗为本文作结,也意在表达我对易竹贤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陈国恩